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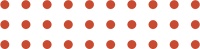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最高检强调,要持续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对于基层检察办案一线的检察干警来说,把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案子办好,把当事人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好,就是最好的“检察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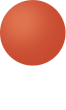

“阿婆,你家现在情况如何呀?儿女都安置好了吗?”当检察官戴璇轻柔的问候从电话里响起,张阿婆立刻精神奕奕地跟她煲起“电话粥”:“有了判决书后,我办事比以前方便多了,儿子阿虎(化名)在精神病院治疗了,女儿阿娟(化名)白天还是在街道的阳光家园接受照料,我晚上接回来就行,轻松多了。”
年过七旬的张阿婆有一双儿女,分别出生于1980年和1983年,虽然早已成年,但两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生活一直无法自理。老伴去世后,张阿婆带着一双儿女住在老房子里。张阿婆有退休金,两个儿女都可以拿低保,居委和街道也重点关注他们一家,时常上门看望,还会定期请人去打扫卫生,原本日子还过得去。
然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张阿婆开始发愁自己百年之后两个儿女如何生活。老人琢磨着:自己有房子可以作为遗产,能不能为儿女们指定一个监护人,比如委托一名可靠的亲戚在自己离世之后照顾他们?
起初,张阿婆想去法院申请。“法律文书我不会写,孩子们也离不开我,我大部分时间都得待在家里。”由于年事已高、法律知识匮乏、诉讼能力较弱,张阿婆迟迟未能成行。后来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2024年6月,她第一次联系上浦东新区检察院,表达了申请支持起诉的诉求。
当时戴璇还没入员额,作为检察官助理跟着“老法师”、检察官蔡琴华接手了这个案子。她们第一时间实地走访了张阿婆家和所在居委,调查核实张阿婆一家的情况。



检察官在居委了解情况
在张阿婆家,蔡琴华和戴璇看到了她的一双儿女。“他们明显存在智力障碍,几乎没有什么认知能力,但老人家很尽心地照顾他们。”戴璇说,张阿婆精神状态还不错,就是担忧一双儿女将来养老问题。
核实了情况,检察官立即与法院沟通。“要为成年人指定监护人,要先宣告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由法院根据法定顺序指定监护人。”戴璇介绍,她们迅速联系了精神卫生中心,带着张阿婆的儿女去做鉴定,很快就拿到了鉴定结果:女儿是智力障碍,儿子是多重残疾,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拿到鉴定意见,张阿婆随后向法院起诉。


张阿婆的儿女在做鉴定
2024年6月26日,浦东新区检察院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2024年9月13日,法院判决宣告张阿婆的儿子、女儿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
此时可以考虑为阿虎、阿娟指定监护人了。《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也就是说,张阿婆应是法定的、首选的监护人。
“当时张阿婆还有些犹豫,是否要专门去申请‘监护人’的身份。”检察官说,“事实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院的判决书是父母作为成年子女监护人的唯一合法凭证。”少了这张判决书,张阿婆想以子女名义办理许多业务时,很有可能无法得到相关机构(如医院、银行等)的认可。
而在这之后张阿婆遇到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儿子阿虎的病情加重,张阿婆不小心摔了一下,骨折了,照顾发病时的儿子愈发吃力。她想将儿子送进精神病院看护和治疗,但没有法律上明确监护人身份的文书,办理各种手续时十分不便。
此时已经入额成为检察官的戴璇仍然关注着张阿婆一家的情况,当张阿婆提出想申请成为子女的监护人后,戴璇认为其情况符合支持起诉的条件。张阿婆老伴(法定的同顺位监护人)的死亡证明文件因年代久远丢失了,她一边前往其原始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调取死亡证明材料,一边协助张阿婆写起诉状,陪同其去法院帮助完成立案。



“如果需要老人出门办理各种手续,我们会特意多带一名干警,还会叫上她的亲戚,专门在旁看护着她的儿女,也是为了让老人家安心。”戴璇说。同时她告诉张阿婆,按照《民法典》第二十九条规定,她担任监护人后,依然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提前指定他人作为以后的监护人,“有了判决书,你就可以顺利地履行监护职责,名正言顺地代理子女处理各项事务了。”
2025年6月,时隔一年,浦东新区检察院再次为张阿婆的案子向法院制发支持起诉意见。2025年6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指定张阿婆为其成年儿女的监护人。在最近的电话回访中,检察官得知,张阿婆已经顺利安置好了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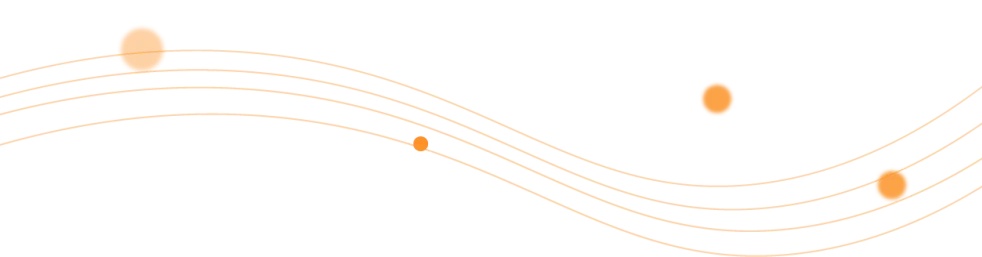
“一年时间,两次支持起诉”是一个个例,也是浦东新区检察院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一个缩影。下阶段,该院还将继续在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下功夫,用更多便民利民检察举措,持续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