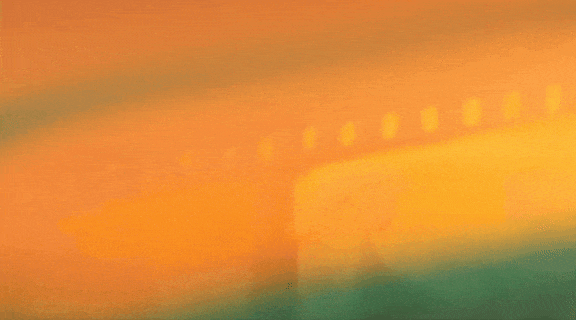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上海艺术评论
上海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上影节”)不仅是中国电影文化的本土盛事,更是一个将全球影像叙事引入城市肌理的“在地化”国际场域。以多层次多视角发掘新锐导演为重点、关注展示高质量影片、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上影节,为各种各样以艺术创造为使命的电影作品提供了与全球观众、评论家乃至发行商深度接触的开放舞台。其中,持续多年的短片竞赛单元近年来获得愈来愈高的关注。随着一年年短片奖项的评选颁发、一场场售磬的金爵短片展映、一次次短片作者与观众的现场交流,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上影节作为一种艺术生产体系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文化政治逻辑,也能更多地从艺术创作的先锋性角度去思考电影短片、尤其是真人短片,如何与上影节的宗旨和选片策略形成积极的平衡态势,以可接受的先锋性参与构建上影节短片的艺术生态,使其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纽带,有效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对话。
在国际电影节的生态系统中,短片长期处于一个矛盾的位置。一方面,短片通常被视为电影美学的实验品,因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大胆创新而备受赞誉。即便在电影技术基础发生着根本转变和融媒体社会背景下,短片的先锋属性仍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在以国际A类电影节和知名的短片电影节为主导的国际电影节场域中,头部电影节圈层非常注重并牢牢把握着对影片艺术品质和社会文化表征的双重要求,进而通过制度化的筛选过程确保入选影片符合电影节的“标记”。而这种过程往往会弱化或夸大短片的激进锋芒。根据皮埃尔·布迪厄和托马斯·埃尔塞瑟的理论框架来看,得到认可的电影短片既是被规训的客体,也反映了艺术家将先锋性嵌入到更广泛的符号资本体系中、积累象征资本的主体选择。
如果说国际电影节与短片之间如果确实存在着一种双向选择的权力博弈,那么今年第二十七届上影节短片单元终选入围的十部真人短片(以下简称“短片”)犹如一组精妙的文化棱镜,既折射出上影节独到的选片眼光,也体现出其作为艺术创新孵化器的筛选标准——在开放包容的理念下,平衡形式探索与文化表达,让短片创作的先锋内核尽量避免产生“被规训”的副作用,转而以“可接受的先锋性”为策略坚守艺术创新的锐度和深度。
01
对严肃议题表达的多样探索
达成“可接受的先锋性”,首先需要回应的是“能否触到世界的痛点?”这个事关艺术家创造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根本问题。所谓世界的痛点,可以理解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面对的深层矛盾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所涉及的社会人文类议题。这类议题往往牵涉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绵延漫长的历史变迁以及立体多维的人物性格,传统上被认为需要足够的叙事时长才能充分展现导演的创作意图。本届入围短片在题材选择上既有对本土现实的深刻观照,也不乏具备全球视野的人文关怀,在议题深度和个体表现细致度方面都秉持着令人惊喜的艺术表现,能够在30分钟不到时间里同时做到触及宏大命题、深入心灵世界、引发情感共鸣。

水之殇|DEAD IN THE WATER
《水之殇》用15分钟讲述了三个人的命运故事。影片的主角是因干旱面临农场存续危机的妇女和因缺钱缺合法身份面临社会死亡的阿富汗难民。这个题材显然放在长片创作中也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多种可能性的宏大叙事。导演莱拉·赫克马特尼亚(Leila Hekmatnia)另辟蹊径,用“执着于已失去的”和“隐身所在的力量”来指代农妇和难民形象的象征含义,从打出泥浆般的井水到毒死农妇的羊等若干具体的情节转折中引发观众对于命运内在真实感受的思考。全片光影设计十分讲究,视听风格凝重而庄严,叙事节奏高度凝练,颇有古希腊悲剧的神采。结尾处,农妇的身影渐渐没入黑夜,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钟声隐约响起,悲悯的哀悼感油然而生。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发怜悯恐惧而使心灵得到净化”的戏剧审美显化为电影的独有美感。

凛冬过后|A STORY ABOUT WINTER
《水之殇》并非脱离现实的“何不食肉糜”,而是导演把身处伊朗的本土症候和跨文化学习经验所领悟的哲学思辨态度相结合,产生了借由古典悲剧内核对现实所进行的寓言式回应。《凛冬过后》的核心则同样扎根于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现实横截面。已经被反复讲述过很多遍的矿区衰落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在导演罗兆光和周楠珺极简化的摄影机调度和安静清冽的声音设计中呈现出别样的美感。湖边、小船、老屋、旧厂不语,男女主角内心一直在微妙地起伏着。导演以充足的耐心等待并凝视两位主角的瞬间情感波动,让告别充满了仪式感,从个人体验升华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时代观察。这样的短片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巨大变迁中个体的变化与成长始终是值得用电影的形式去观察和记录的,并且在短片中有可能得到更加细致入微的呈现。

记忆之泉|THE FOUNTAIN OF MEMORY
《记忆之泉》则是一趟以西班牙战争创伤和家族记忆为纽带联结而成的未知旅途。胶片画面显影着独特的电影美感,仿佛常常陷入时间的凝滞,暗场和剪影的交错光效像闪电撕开沉睡的意识。念日记的内心独白和林中的泉水声则时刻提醒着我们视点的交叉和时间的流逝。全片的高潮部分是山洞里无光的纯黑段落和闪光灯交错映照出的茫然脸庞。这个段落与片尾两张对峙凝视而无声流泪的面孔对应起来,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呐喊。
02
对多元文化价值的平等共享
“可接受的先锋性”也需要在电影节提供的文化交流场域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发共情作用。在信息碎片每天不间断轰炸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关照有加?是否对身边的人和事缺乏共情?是否对天涯海角和沧海桑田也只有零散的、三言两语式的了解。电影短片是可以再次唤起观众对这一切的兴趣,带领观众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审美的眼光去体验这份间接经验,拨开刻板印象的迷雾和碎片化信息摄取的惯习,去关注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思绪,在黑暗世界的幻影匣子里看见真实。本届入围短片不仅有严肃深刻的观念讨论,也有在文化交流层面的真诚分享。创作者们主动意识到平等之于分享的重要性——唯有消解文化等级的预设,才能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深度交流。

电竞恋爱白皮书|VIDEO GAME AUTHOR
墨西哥导演切马·诺韦洛(Txema Novelo)在短片《电竞恋爱白皮书》中特地设计了一段情节,让女主角在安排著名游戏设计师和来自墨西哥的男主角见面的时候,全程绑住设计师的双手。面对男主角的疑惑,女主角真诚回应:“这不就是墨西哥人的谈话方式吗?”在这里,导演想表达的是:这不就是对墨西哥的刻板印象吗?这部历时7年才得以完成的短片,二次元的风格怪诞十足而充满黑色幽默,却是在温和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关于文化权力的当代冷笑话。

世界的尽头|THE END OF THE WORLD
秘鲁导演《世界的尽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对非常古老的概念:生与死。曾是一场巨型山体滑坡幸存者的老人正在步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回忆起数十年前的那场灾祸,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咏叹。影片以老人的视点贯穿始终,主体段落中缓缓移动的长焦镜头描摹出老人的童年回忆:静默无语的高山与活泼嬉闹的孩童,黑白画幅中的老人则用非常规构图的固定镜头来表现,出现在一头一尾。镜头语言处处凸显人与自然的原生态关系,尽量消解了可能对秘鲁山民产生的猎奇眼光,以一种缓缓流淌的生命意识拉近了观众和老人的心理距离。

阿利亚的吉尔巴拉|CHILDREN OF THE LAND
冰面与雪山,速滑与马车,对于导演胥瑞来说不是民俗风情而是生活日常。他用“辽阔的故乡,轻轻承托着小小的我们”来概括影片《阿利亚的吉尔巴拉》所讲述的关于友情和成长的故事。影片正是以院线长片级别的视听完成度弹奏了一曲充满悬念的少女心事与乡愁抒情的复调叙述,触发了观众的人生经验和少年回忆,让观众对阿利亚和吉尔巴拉都有了强烈的带入感,引发了一次对归家与出走的自我询唤。
03
对电影作为艺术的持续突破
“可接受的先锋性”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化指标,而是短片作者从无到有逐渐开拓电影作为“世界语言”新边疆的动态过程。既不被传统审美范式所束缚,也不沦为纯粹的形式游戏,而是在媒介自觉与文化自觉的辩证统一中,构建起跨文化对话的有效通道。本届入围的短片不仅在视听呈现度上都达到了很好的水平,也在更高一层的观念中对“电影艺术是什么”进行了积极的解答。

野鸦|CROW
《野鸦》选取两种画幅构建了童年、母亲与相机的三个视点来讲述男孩与亡母灵魂的重逢旅程。山间的大雾和傩戏面具的反复出现赋予了影片强烈的非现实气氛。正如导演徐简明所提到的,他善于融合诗意叙事与空间结构,探索个人经验中的神秘主义。影片的观影感受不仅仅是在描绘“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孤独、死亡,如何去理解爱和记忆”的现实问题或者某种具有共性的宏大议题,而是在表现孩子初识孤独与死亡的瞬间、以及感受到来自母亲温柔注视的时候,让观众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期待感和不安全感。

无人知道我消失|NO ONE KNOWS I DISAPPEARED
《火车进站》给世界上第一批观众带来的震惊感受揭开了动态影像模仿现实、再现现实的历史新篇章。电影短片所能给观众的新的审美感受根植于短片的时间容量所能对真实进行的再现和表述。可以说是按照从巴赞“完整电影的神话”到德勒兹“时间-影像”“空间-影像”的方向在摸索前进。《野鸦》所展现的对于三个视点的分割和拼贴是一种摸索。《无人知道我消失》则借助公路片的类型模式,用精准的镜头调度和声画配合把电影的造型功能推向某种极致,从而对电影叙事的边界发起冲击。《远去的若娜》和《朱迪,或第一次背叛》也都是在充分展现电影语言现有约束下的美感形态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造型-叙事突破。

远去的若娜|JOANA IS LEAVING
正如托马斯·埃尔塞瑟对“驯服的视野”这一理念的概括,具有“可接受的先锋性”的电影短片往往是符合电影节审美规范的创新版本,即形式上富有创新创意但并非难以理解,具有社会批判性但并非结构性破坏,具有实验性但又被精心策划以赋予文化合法性。同样,珍妮特·哈伯德将电影节视为中介空间。在这里,激进的形式被转化为可在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国际视野的观众中传播的文化消费文本。因此,电影短片中“可接受的先锋性”代表着一种张力:介于真正的审美颠覆、电影节对艺术维度考察和观众认同之间。

朱迪,或第一次背叛|JUDITE, OR FIRST REBELLION
综上所述,当我们在国际电影节语境下评估电影短片的艺术品质时,尤其应当多加关注即创作者在体制边界内策略性运用形式创新、达成叙事和表意的创新的艺术作品。这种实践既挑战又强化主流美学惯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电影节作为结构化文化场域,通过符号资本的分配机制,选择性地将符合特定创新语法的前卫形式合法化。这种体制性认可往往将潜在的颠覆性艺术实践转化为“可接受的先锋性”,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边界,也让国际电影节搭建的文化传播平台得到延伸。
很多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作者都会有和莱拉导演相同的愿望: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触动观众,即便银幕熄灭之后,它的情感依然能长久留存在他们心中。这种对影像持久力的追求,恰恰揭示了电影艺术的本质魅力——它不仅是转瞬即逝的光影魔术,更是能在观众心灵深处生根发芽的情感种子。作为本土观众瞭望世界的窗口,也作为全球影人感知中国的门户,期待上影节在短片单元继续发力,继续将来自天涯海角的优质影像带到每个创作者和观众触手可及的“家门口”,在鼓励电影艺术创新求变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跨文化传播的情感共鸣圈层。
本文作者:沙扬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
青年影像传播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