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我有幸随上海市作协前往罗丹艺术中心采风。这座由上海世博会法国馆改建而成的展馆,外围网格式构造如一张流线型的白色大网笼罩,为这座艺术圣殿蒙上一层神秘面纱,静候访客开启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步入大厅,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厅内一尊被玻璃罩盖着的罗丹石膏像,作品中的罗丹须发飘逸,深邃的目光坚定地注视前方,充满对艺术的执着与挑战。
讲解员介绍,展览按6个主要章节和2个特别章节展开,汇集了雕塑、绘画、陶瓷、影像等106件作品。有6件被法国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作品,展品件件皆为真迹,且有其首次亮相的珍品。
展览循罗丹艺术生涯展开。青年时期作品人物形态饱满、细腻圆润、栩栩如生。这些作品是青年罗丹师从阿尔伯特·恩涅斯特·卡里耶·贝勒斯后,于其工作室亲手雕刻的。
步入罗丹的成熟期作品区,其中展示了《青铜时代》《夏娃》等经典之作。《青铜时代》是罗丹第一件完全独立完成的作品——青年男子身材健硕,双目微闭,一手抚头,一手握拳,似乎是在冥想与追悔,欲迈步的瞬间,凝固着新古典向现代的过渡。因为作品过于逼真一炮而红,成为罗丹的成名作。《夏娃》的原型则是位孕妇,她双手抱头低垂,身躯佝偻蜷缩,浮夸的大手深陷肌体,原始的原罪感与耻感穿透石质,直击人心。
罗丹雕刻的不仅是形体,更是灵魂在命运重压下的呻吟。其艺术绝非唯美珍玩,而是刺穿精神迷雾的强心针。他自称是“真理的猎手和生命的守望者”。
晚年罗丹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思想者》初稿中达到顶峰。这件首展且首次出国的法国特级文物,在高72厘米的彩色石膏上凝固着罗丹的指痕。不同于后世青铜版,它更具血肉温度:壮硕男子弓坐,微垂头颅,放松的右手与紧绷的左腿形成微妙平衡,仿佛正从沉睡中觉醒。罗丹宣称:“我的《思想者》用每一块肌肉思考。”作品中青年硕大紧绷的脚趾紧扣于泥地,强有力的手背顶着下巴,深锁的眉眼坚定地注视着前方,身体每个部位的肌肉都显得铿锵有力,透露出对生活的反思和未来的畅想。不同于古典雕塑追求的完美比例与理想化姿态,罗丹捕捉的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既有初生的懵懂,又蕴含着觉醒的力量。
《地狱之门》则是其残缺美学的集大成者。依托十字架构筑,186个人物在未完成状态中迸发震撼力量,扭曲的肢体与痛苦面容,熔铸成挣扎绝望的地狱图景,警醒世人“有可为有所不为”。
除了对地狱图景的隐喻,罗丹晚年更聚焦于人性的崇高与挣扎。《加莱义民》的6位赴死者姿态各异,脚下保留未琢石块,仿佛自大地诞生又将回归尘土。
在最后独立展区的《吻》令人震撼——一对拥吻的恋人,激情瞬间下潜藏着疏离——嘴唇相接,身体纠缠,脚趾却微微退缩,双手稍显迟疑,揭示了亲密关系中无法消弭的孤独鸿沟。
特展区“罗丹的中国情”让人感慨。16件罗丹珍藏的隋唐陶俑、明代青铜观音、清代瓷器静静陈列。他虽未踏足中国,却敏锐捕捉到中国艺术线条的韵律与留白哲学,印证了“艺术无国界”的真谛。
走出艺术中心,重返夏日阳光,雕塑带来的震颤犹在。罗丹以其不可磨灭的粗粝与残缺之美,在都市喧嚣中投下深邃阴影。我们不仅触摸到罗丹的艺术灵魂,也重新审视了自身对美、人性与艺术的认知。在凝固的雕塑中,生命的跃动与永恒的力量,已然长存。
撰稿:邓登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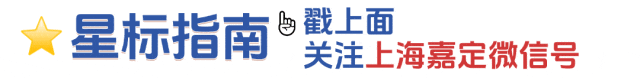





点赞分享给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