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文联文艺家大讲堂 7月10日下午,2025年第三期“上海市文联文艺家大讲堂”在文艺会堂多功能厅举行。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施忠教授,为大家带来“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主题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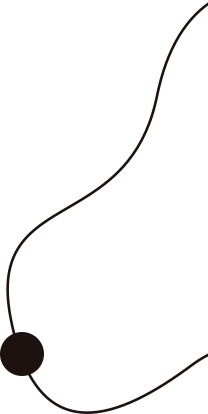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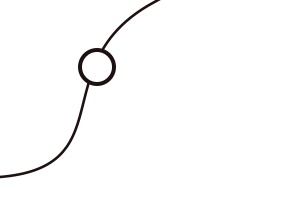
钢琴自明朝末年传入中国,最先作为宫廷、教堂等特定场合演奏乐器,直至新文化运动后,钢琴走向民间,成为中国人学习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讲座以钢琴为例,介绍近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如何用西方乐器讲中国故事,将中国特色融入音乐创作中——

西方的古钢琴来到陌生的东方古国
施忠教授首先给大家科普了中国最早的钢琴教师和“琴童”。最早在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了一种名为“Clavichord”的机械古钢琴,标志着西方键盘乐器正式进入中国。四个太监成为首批学习这种乐器的学生,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沃则成为了他们的老师,开启了中国最早的钢琴教育。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对西方科技和音乐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亲自学习古钢琴演奏技术,甚至能够用它弹奏中国传统曲目。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钢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通过五个通商口岸传入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教会学校的出现,民间开始有了初步的钢琴教学活动,但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
真正让钢琴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是20世纪初期兴起的学堂乐歌运动。这些歌曲结合了欧美或日本旋律与中国歌词,在学校中广泛流传,促进了钢琴作为伴奏工具的应用。此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多个音乐社团,其中不少都设有钢琴课程。比如著名钢琴家李翠贞的故事表明,早期学习环境如何影响个人成长及后来的专业成就。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钢琴逐渐普及到普通家庭之中,电子钢琴和数码钢琴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老年人群体对于学习钢琴的需求日益增长,反映出人们对艺术追求方式的变化趋势。同时,随着艺术教育的普及,如今中小学生掌握钢琴技能和乐理常识已不再罕见,这体现了整个社会音乐素养水平的提升。
可以说,从最初由传教士带入宫廷的小众娱乐项目发展成为今天深受欢迎且具有重要地位的艺术形式之一,钢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音乐生活,而且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此外,通过对绝对音高形成关键期的研究发现,四至七岁是儿童学习固定音高乐器的最佳时机,这对未来音乐才能培养至关重要。
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与钢琴教育
施忠教授表示,上海在中国音乐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北京女子高师音乐科、北大音乐传习所、北大的艺专音乐科及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等中国早期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奠定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基础。例如,行知艺术师范在20世纪80年代以陶行知的名字重新建立,其历史可追溯至1923年的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7年,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在上海建立,标志着中国钢琴教育进入专业化高水平时期。
近年来,施忠和他的学生们非常重视口述史的整理工作,由他们整理并出版的《上海音乐名师成长录》,记录了17位基础教育正高级特级教师的经历,这对于研究和践行中国的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施忠表示,上海音协也做过一系列名师名家相关记录,这些对于留存上海城市音乐文化发展历史意义重大,像周小燕、葛朝祉、温可铮、曹鹏等名师名家的事迹都值得整理。而最早一批外国钢琴教师培养了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如梅百器培养了傅聪,他们的教育经验也值得参考。我们应该重视古今中外音乐教育史料的记录、研究和科学运用,以更好地发展中国音乐教育。
上海是中国钢琴艺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发源地,自20世纪30 、 40年代至今培养了大批人才,中央音乐学院的不少钢琴家、教育家都来自上海。1951年至1964年,我国有13名钢琴家在20次国际比赛中获重要奖项,如傅聪、刘诗昆、顾圣婴等。80年代后期,郎朗、李云迪、李坚、孔祥东等新一代钢琴家成长起来,这得益于中国越来越好的音乐文化生态。在非专业钢琴教育领域,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钢琴进入寻常百姓家,近年来虽然都在说“钢琴热”有所降温,但学习人数并未减少,甚至可以说,如今的家长和学生对钢琴学习的诉求和目的性都更理性、更回归艺术了。
中国钢琴曲——新奇的音响世界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始于20世纪前20年的探索期,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是首部中国钢琴作品,虽旋律、和声具西方风格,尚未展现出中国特色,但它开启了中国人创作钢琴作品的先河。30年代,美籍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在上海举办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的创作比赛,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获奖。《牧童短笛》以中国五声音阶创作,运用“同头异尾”等中国旋律发展手法,结合西方复调技法,将中国音调和西方作曲法成功融合;《摇篮曲》在和声中加入特色音,凸显中国风格。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作曲家注重将中国民族音乐融入钢琴创作。丁善德的《儿童曲集》如《快乐的节日》《郊外去》等,充满童心与经典韵味,深受乐迷喜爱。此外,还有根据民族器乐曲、民歌改编的作品,如《水草舞》《三六》《采茶扑蝶》《彩云追月》《春江花月夜》等,这些作品或借鉴民族乐器手法,或融入传统音乐元素,展现中国特色。王建中改编的《百鸟朝凤》极具创意,既保留了原唢呐曲的旋律特色,又充分运用了钢琴演奏技法中的倚音、颤音、琶音、泛音等手法,生动地表现了鸟鸣和自然界的音响色彩效果。
《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序曲与舞曲》虽创作于特殊年代,但艺术性与民族性结合出色,融入高山族音调,模仿锣鼓节奏,兼具复调成分。20世纪80年代后,钢琴创作形式多样:有用民族器乐曲、声乐曲改编的;有用民族音调节奏创作的,如基于朝鲜族节奏的作品;有用现代作曲技法追求民族神韵的,如陈怡的作品;还有用独创技法创作的,如《太极》等,展现了中国钢琴音乐在“吸收外来、不忘本来”基础上的多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施忠特意带来三位得意门生,给大家现场演奏了他所介绍和分析的钢琴作品。从这些年轻人投入的状态、精湛的技艺和享受的神态上,我们亦看到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繁花与硕果。
在讲座最后,施忠表示,尽管钢琴是一件外来的乐器,但我国近百年的钢琴演奏、教学、创作的实践与历史证明:播种在我国独特民族文化传统土壤中的外来乐器、外来文化是完全能够为我们所消化、吸收,并生长出具有独特神韵和无限魅力的音乐文化硕果的。现当代的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交流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自信、勇气和探索中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