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26日,69岁的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音乐人类学家高文厚(右二)与“花儿”歌手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二郎山上交流。他渴望将这份来自中国西北大地的瑰丽歌声推介到海外,让世界听见。
提到荷兰,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郁金香、风车和奶酪——这个国土面积还不及江苏一半的小国,却以全球1/40的耕地,创造出世界第二的农产品出口额,堪称“弹丸之地,喂养世界”。
也有人会想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这家几乎垄断全球高端光刻机市场的企业,总部就坐落在被称为“荷兰硅谷”的埃因霍温。
但少有人知道,荷兰还是欧洲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其中的莱顿大学,是荷兰当代中国研究的重镇。
今年5月中旬,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莱顿大学,笔者随团担任翻译。此次经历让他对如何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多思考——关于语言的边界、理解的落点,以及“讲述中国故事”的难处与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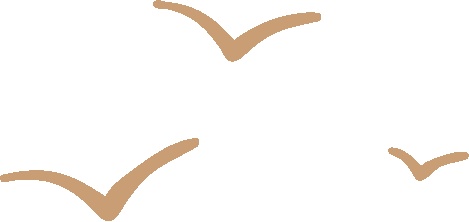
5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们驱车从阿姆斯特丹前往莱顿。阳光在云层后时隐时现,车窗外的风景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澈。半小时后,阿姆斯特丹的都市气派还未完全褪去,莱顿的静谧气息便已悄然铺展开来。
初到莱顿大学,一切似乎都慢了下来。数条运河交错,静静穿城而过。学校没有大门,红砖教学楼散落在绿树掩映间,与周围街区自然相连,没有任何界限。不同肤色的学生们骑着自行车轻巧穿梭。站在拥有全欧洲最大中文藏书量的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前,我心下暗叹:“真是个做学问、搞研究的好地方。”

莱顿的运河
我早知莱顿大学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声望,却仍被它的学术气氛所感染。这里被称为“欧洲汉学重镇”并不夸张——早在19世纪中叶就设有中文专业,后来又陆续建立了汉学研究院、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等专门机构,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研究学者。可以说,荷兰的中国研究大半倚赖于这所大学数百年的持续耕耘。
如今,莱顿大学已拥有多个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学术平台:区域研究所下属中国研究中心、国际亚洲研究所,以及专注政策研究的莱顿亚洲中心。它们的研究议题横跨古今中外:从帝制时代的书画与佛教政策,到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城市治理;从移民研究,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欧经贸关系……在这样一座安静的小城里,关于中国的故事、中国的话题一直在被热烈讨论,反复思考。
交流开始前,我们在莱顿大学亚洲图书馆简短参观了一圈。同行的几位专家打趣说,像是走进了“汉学圣地”,而接下来的交流,也确实不乏思想的碰撞。

莱顿大学校园一角
此次代表团四位专家带来了四个交流主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脱贫攻坚与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中国外资流入变化与高质量发展”及“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建设与社会发展”。这些选题既回应了当下中国内部的发展议题,也面向全球关注的方向,专家们希望通过扎实的学术逻辑、鲜活的数据和清晰的政策脉络,提供一个更具体、真实的中国图景,同时也很想了解当下荷兰学者、欧洲学者如何观察和认识中国、认识上海。
与笔者以往参加的一些国际会议不同,莱顿的交流氛围没有那么强烈的对抗性——更多的是提问、追问,以及某种若即若离的兴趣。从海外学者们的发言中,我们能感受到欧洲中国研究与美国路径的不同:欧洲不太强调“战略竞争”或“制度冲突”,更多是从区域研究、人类学、文化史的视角切入,用理解而非判断的方式观察中国。
但这份“理解”并不等于认同。在交流中,一位学者双手抱臂,用略显质疑的语气提问: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否意味着试图将自身的发展路径输出,是否会带来新的不平等?我注意到她提问时几乎没有看我们代表团的成员,而是注视着空中的某个点,仿佛在质问一个抽象的中国。
对此,中方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平静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国情、同时也注重借鉴各国的经验和现代文明而探索前进的。我们当然不会把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模式简单‘套用’到别国身上;只是希望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尚未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分享我们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借鉴和参考,我们当然也会积极借鉴和参考外国的好经验。”
略微停顿了一下后,他接着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有过简单照搬前苏联发展模式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也不希望、更不会要求其他国家简单套用中国模式,大家可以相互学习交流,毕竟,世界各国的文明可以交流互鉴,这就是中国的理念。”
听到这里,那位提问者的神情微微一变,目光转向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双臂也悄然放下,目光中闪现出明朗和信心,随后若有所思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原来,这种现场的回应,有时比书面材料来得更加有效——既是澄清,也为进一步的理解与对话打开了空间。
对我而言,这些经历反复提醒着一个现实: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能被世界听懂。
这一点,在莱顿的交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议题,听起来像是政治表述,但代表团的几位专家并不是就概念讲概念,而是用各自熟悉的研究路径——发展经济学、社会政策分析、外资流动数据、儿童保护机制——把这些概念背后的学术化表达、学理性阐释娓娓道来、层层展开。正是这种以学术语言来“翻译”中国议题的方式,引起了在场学者的兴趣与回应。
我记得现场有位外国学者在提问时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否可以从中国历史中追溯出一种“历史基因”?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真正能够引发深入交流的,并不是某句口号,而是我们是否有能力通过案例、数据、逻辑以及国际化语言和方式将这句口号背后的中国讲清楚、讲得可信。
这次莱顿之行还有一个小插曲。国际亚洲研究所的负责人在交流时和我们闲聊,说他本人已经很多年没能再到中国,资金是最大的问题。疫情之后,荷兰教育部削减了对区域研究的支持。他笑着说:“我们有的是兴趣和研究议题,但缺的是机票和经费。”
这让我再次意识到,面对面的交流是真实可感的,面对面的探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无论是国际亚洲研究所的联合研究平台,还是上海社科院的青年汉学家项目,哪怕只是一段短暂的学术访问,它都意味着,面对面交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而不是把彼此当作“研究对象”或“政策议题”。
离开莱顿大学前,我们在国际亚洲研究所门口的一块红色海报旁合影。我瞥见上面写着“Connecting Knowledge and People(连通知识,连接人类)”。在这座静谧的小城里,这句话竟意外地有种力量。
我想,也许我们与世界对话的第一步,不是去强调中国有多么与众不同,而是用心说清楚我们今天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虽然短暂,却往往更能触及观念深处。一问一答之间,不只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认知方式的碰撞与磨合。比起对彼此立场的判断,更宝贵的是双方愿意在语言与逻辑中找寻共同的理解起点。也许,这正是今天讲述“中国故事”真正的难处与希望所在——不是要改变谁,而是要让复杂的现实被看见、被听懂。
作 者:

邹 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项目官、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生
来源:解放·上观:海外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