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作家鲁引弓携新书《小欢喜2:南京爱情故事》来宁,为6年前的热播剧《小欢喜》开启续篇。上一部《小欢喜》剧终时,方一凡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剧专业,乔英子也拿到了心心念念的南京大学天文系录取通知书。
“《小欢喜》不仅包揽白玉兰奖、飞天奖、金鹰奖,还带火了南大天文系,让这个冷门专业的报考率大幅攀升。在南大,就连留学生都知道有位‘校友’叫英子。”鲁引弓笑言。这几年,读者观众没少在线催更,一再叮嘱他:“续集要写甜一点哦。”提笔创作时,鲁引弓却犯了难——他发现,闯过高考的难关后,孩子们遇到了更多的人生课题。
来南京寻找“人生解法”
《小欢喜》的故事为何转入南京?
其实,对“凡英”选择怎样的院校专业,鲁引弓暗藏了不少“小心思”:南大天文系在全国高校天文专业中位居TOP1,匹配英子的学霸地位;远赴南京意味着摆脱母亲的过度控制,天文专业又象征着头顶的一方星空,和心中的浪漫幻想。至于方一凡考入的南艺音乐剧专业,和中戏、北影相比算不上顶流,却恰恰折射出这位“阳光大男孩”的人生哲学:人不一定非要站在舞台中央,只要心怀热爱,也能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闪闪发亮。

看到英子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南大,读者们松了口气,上一季英子遭遇的“教育焦虑”让人心有余悸:母亲宋倩不仅拼命“鸡娃”,还不允许女儿报考外地高校,导致英子一度抑郁。网友在弹幕上心疼地留言:“这个喜欢天文的孩子,眼中却没有了星星……”
在鲁引弓看来,经历过兴衰荣辱、把“多大事儿啊”嵌入城市性格的南京,能够为小主人公们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节奏,和看待人生的多元视角。
“每次来南京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这回,鲁引弓在南京连住了几天,“这里街道疏朗开阔,因为地处南北交会,城市性格里有种北方的大气。南京年轻人没有那么精明内卷,急吼吼地‘向钱看’;写作者也从容,笃悠悠地在那里写,没想着非要成功成名。在南京,似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儿适合年轻人适度地慢下来,从而为打破优绩主义的迷思提供了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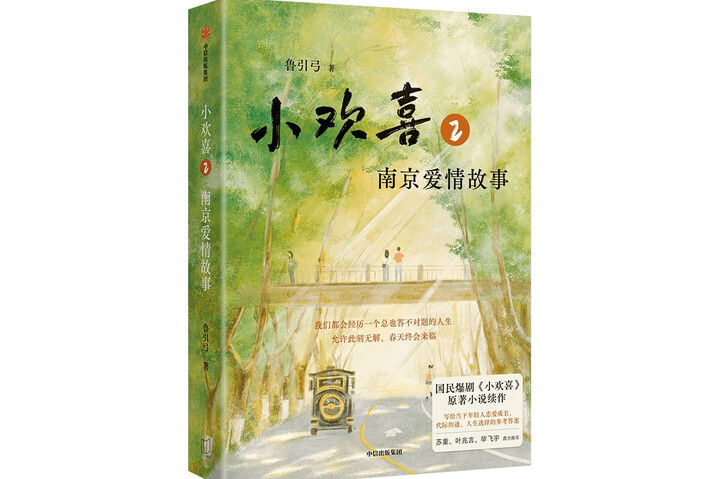
方一凡和乔英子,一个在市区,一个在仙林,他们怎么擦出爱情火花?写作期间,鲁引弓在线求助,南京读者纷纷支招,让他隔屏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友好。
这次,鲁引弓走进鼓楼区白云亭文化艺术中心举办新书分享会,这里也是热播剧《我的后半生》的取景地之一,“没想到一个区级图书馆的氛围这么好,途中没有一个读者走掉”。此外,南京还有红山动物园,有很多livehouse和原创乐队,几年前他来宁采访时,发现这儿的剧本杀市场特别活跃:有个南艺音乐剧专业学生就在校门口开剧本杀门店,还有学生业余为剧本杀写剧本,一个剧本就可以赚几千块,“年轻人太有想法、太厉害了”。

于是,在鲁引弓脑海中,如何“跟着方一凡玩转南京”,“学渣”怎么帮助学霸调剂生活、重拾快乐的能力,一下子就融入了南京城的烟火图卷。
给年轻人一个“深呼吸”
《小别离》《小舍得》《小欢喜》《小痛爱》构成了鲁引弓的教育“四重奏”,覆盖了幼升小、小升初、低龄留学和高考等诸多阶段。但对他而言,教育仅仅是表达的载体,他引弓想要射中的靶心,一直是当今社会弥漫的优绩主义。
“哲学家韩炳哲为什么那么火,他提出的‘功绩社会’‘自我剥削’直指时代症候。还有黑塞《悉达多》近年来翻红,因为它本质上讲的是一个人穿越世事之后找到自己的故事。”鲁引弓对记者说。
怎么定义“绩”,如何评判“优”?在优绩主义的陷阱中,存在着“用一把尺子量人”的现象。《小欢喜》中,这把尺子是成绩;《小欢喜2》中,尺子变成了“你的专业好找工作吗?你能考研考公考编、顺利上岸吗?你的简历刷够了吗?你工资收入怎么样?你家里有几套房?……”

正因如此,“凡英”之间的双向奔赴遭到了英子母亲的反对。作者借方一凡之口表达了对这种理念的反思。在乔英子、林磊儿这两枚学霸身上,鲁引弓也真实表达了他们面对“骨感”现实之际的激情退潮和人生困惑。
林磊儿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本科生,纠结于是否读研读博、成为一名“青椒”,这份努力是不是具有性价比。在乔英子身上,鲁引弓注入了作为角色原型的两位南大天文系学生的真实际遇:本以为天文意味着流星、陨石和外星人,结果变成了无穷无尽的高数、物理和星轨计算;在天才云集的拔尖班里,自己的星光如此黯淡,一不留神就有垫底的危险。当焦虑弥漫为校园里的空气,到底什么是学习的意义,什么是理想的价值?
“别怪磕糖不甜,我没法撒工业糖精,只能给你一颗‘酒心巧克力’——你要穿越生活的苦,才能找到深处的那一抹甜。”鲁引弓笑道。

如何找到这一抹“甜”?鲁引弓呼唤“价值观的解放”:“我身边就有大厂高管离职后,到咖啡馆工作,为人生松绑,从‘轨道’走向‘旷野’的故事。”《小欢喜2》中,“不卷”的方一凡为学霸女友创造快乐,他自己也找到了脱口秀演员这一“超绝适配”的职业方向。借着“方猴”带来的欢乐,作者想给那些戴着隐形枷锁的年轻人一次畅快的深呼吸!
“轨道”之外有什么?还有“家”的系统,有亲人的守护,人与人的连接。作品中方一凡父亲方圆的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他不仅为身边人建构了一个松弛快乐的大气层,还充分发挥喜欢聊天的长处,失业后成了社区里的热心调解员。鲁引弓说,我们时代其实有很多舞台,就像天空中除了织女星、北极星这些最亮的星,不是还有很多星星也在发光吗?
剧外有真正的“小欢喜”
从电视剧《小别离》到《小欢喜》《小舍得》,“小系列”部部都是爆款。
在鲁引弓看来,爆款的密码首先在于它们涉及的社会议题,这和他作为前媒体人的敏锐捕捉有关:“不管是教育,还是《小宅门》聚焦的房产,手头上《小饭碗》关注的就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把这些议题化大为小,透过千家万户的那扇窗去看,看屋檐下的焦灼困惑,也送上治愈的暖光。透过这些作品,我想鼓励人们在大时代里做一个勇敢快乐的普通人。”
在文学母本“打底”的基础上,主创们的二度创作激发了原著的生命,与之碰撞出“化学反应”。《小欢喜》中,黄磊、海清、陶虹、咏梅、沙溢等一众戏骨狂飙演技,让鲁引弓叹服不已:“黄磊他们太了解这个时代的接受美学了,把有些沉重的原著变成了喜闻乐见的轻喜剧,和一抹含泪的笑。就连英子母亲这个不讨喜的形象,也被陶虹用她的表演艺术给化解了,让观众在批评她的同时,也同情她、理解她。”
让身处不同代际的观众可以“同屏追剧”、理解彼此,从荧屏光影中汲取生活的勇气,是鲁引弓的创作理想。作为60后,他特别希望和年轻人交朋友,采访中他一再提到,自己如何被年轻人身上的光芒所照亮。
“和南大天文系的同学们座谈,孩子们眼睛里的光,他们言谈的成熟,举手投足之间的修养,还有对科学的热爱,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鲁引弓感叹,“打动我的还有他们的善良热情,‘有事您随时喊我啊’‘需要群演的话我来啊’,听说我带着新书回南大,当时采访过的孩子竟然专门从外地赶来……”

鲁引弓和乔英子的两位原型合影
《小欢喜2》结尾,乔英子重拾对天文的热爱,跟随学校团队赴青海为望远镜选址。那么,真实生活中的“乔英子”怎么样了?
“距离上次见面四年过去了,乔英子的两位原型还在南大,一个是研究生、一个是博士生。四年,我们还没走散,还在这里。”鲁引弓激动地重复了几遍,“我们还没走散,他们也没有和自己的理想走散,这是真正的小欢喜。”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