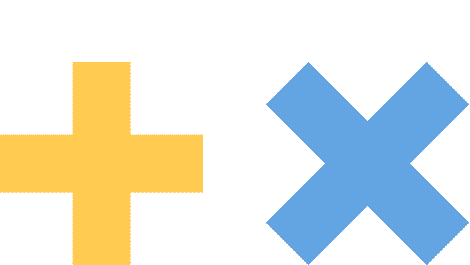
闯上海,创巅峰,青年与城市共成长!
上海市青年五十人创新创业研究院与第一财经联合制作推出《科创Z世代》之“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专辑”,通过讲述上海青年奋发引领未来、笃行青春之志的故事,探寻上海这座青年发展型城市与创新创业青年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创新密码”。
今天,来看上海宾通智能科技创始人龚超慧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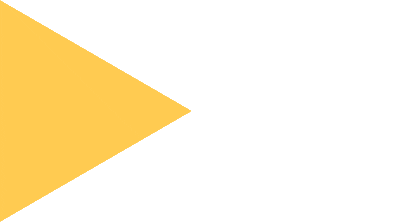

视频时长:5分53秒
主持人:如果咱们今天就来到了工厂,体验在工厂打工的一天,那“最强大脑”是怎么样具体运作的?
龚超慧:一讲制造大家都觉得是在产线上打螺丝,但其实工厂中有很多的智力活动,供应链的计划管理、生产计划的管理、仓储的管理、出入库的作业、生产指令的派工,这些其实都是由大脑完成的。
主持人:它在这个工厂里又是协调员,又是调度员,又是管仓库的,又是管产线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龚超慧:对,我们有一些客户,他的供应链中心原本有数百名的计划人员,他要去考虑订单的交期,当前生产的排期。原本每周他们要循环作业数百人的时间,现在只需要几个人,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够把一个生产计划和编排作业全部都做完了。
主持人:是不是因为用了“最强大脑”,下订单的时候或者制造的时候,就不会存在积压了很多这样的情况?
龚超慧:它能够精准地做市场需求的预测,能够合理的安排生产计划、库存准备,能保证所有的生产一定能够尽最大的可能被市场消化掉,能够变成经济收益。
主持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这件事?
龚超慧:我算是一个“厂三代”。我母亲原本就是在我父亲的工厂里面管仓库管物资的,所以从小就是在仓库中耳濡目染,看着工人每天领料。我母亲每天都在做大量的表单记录,下班还特别晚,要去整理所有出入库的数据,盘点仓库里面剩余的物资,有的时候缺料了,十万火急被别人追得赶紧去救火,当时其实就对这样的一个运营场景和环境充满了好奇,就对工业工程很感兴趣。我本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机械工程方向,读博士的时候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去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算法的研究。
主持人:从机械到算法。
龚超慧:对,到了博士的后期会发现,我们正在从事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学的技术,很多重大的问题是在工业中先产生而不是在学术圈,所以当时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创的时间节点。
主持人:一开始创办公司,公司就叫宾通智能了吗?
龚超慧:对,我们这个公司的英文名称叫BITO,它是两部分的组成,一个是比特bit,因为数字世界是由比特组成的,一部分是o代表一颗原子,物质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我们相信人工智能技术,它本质是两个世界的连接。
主持人:当时在国外这家公司运营了多久?
龚超慧: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决定全部回到国内。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市场,有最快速、最敏捷、最全面的供应链体系,只有在这样一种有极致要求、有最高复杂度的应用场景下,才能更好地去打磨产品。
主持人:回国之后,为什么最终把地点就落在了上海?
龚超慧:这件事情是需要长期主义的,它需要非常良好的产业沉淀,上海有深厚的产业积累,再结合它全球化的视野,能够去承载很多最前沿的科技研发。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你在2024年“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获得了“上海青年科技创业年度十大先锋”的称号,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鼓励?
龚超慧:创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能够看到外部有认可的声音,这对我的团队、对我的产业链上下游都是一个重要的鼓励。
主持人:以前你是一个做科研的博士后,再到成为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你觉得转变丝滑吗?
龚超慧: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坎坷的,我们做了很多的试错。科学家创业,他很多时候都是从自身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这样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因为有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技术,认为自己应该也要去造硬件,但却忘了中国有强大的产能、非常好的制造供应链,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个已经过剩的事情或者高度竞争的事情,我们应该去填补市场的空缺,去增值和去放大整个产业价值。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主持人:有什么事是你下了工厂之后,发现和自己在办公室里想的不一样?
龚超慧:像我们跑去客户的一些现场,给他安装实施机器人的时候,发现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充分地评估客户的货物大小,就导致机器人在有些场景用不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纸面上照本宣科地跟客户去讲,可能缺这个数据,缺那个数据,到底是谁的责任问题,可能就没有良好的答案。但我们真跑到现场,设身处地实际去看应用场景,我们就能知道我们要考虑它下面有没有带着一个托盘导致它高度的变化,都必须很严谨地去把它考量到。当我们如果抱着一个学者心态和技术创业者的心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我们就不能理解对方的视角,很容易做出错误的产品。
主持人:我们最后来放开想象,智商情商都拉满的工厂,离我们还有多远?
龚超慧:其实有一些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像汽车产业,它的个性化选配、个性化程度比也开始越来越高。我相信在接下去三到五年的时间内,更多的行业会有这样的底层模式变化,能够更加精细地、更个性化地为市场提供服务。
主持人:当所有的工厂都有了这样一个超级大脑,咱们中国的工业化的终极形态是什么样?
龚超慧:有点像是一个大型的自动贩售机,上面运行着超级工厂大脑,同时又是网络化连接的。可能明天你要去一个主题聚会,可能你在一个APP上和AI助理讲你的需求,这个时候它就通过AIGC的手段,自动地帮你设计了一款衣服,可能就在你家楼下一个小的生产设备当中自动地裁缝,等你第二天要去聚会的时候,下楼取一下衣服就可以。
主持人:真正地就走进我们的生活。
龚超慧:对,为整个社会提供柔性的、个性化的生产力能力,这是未来的一个终极的智能制造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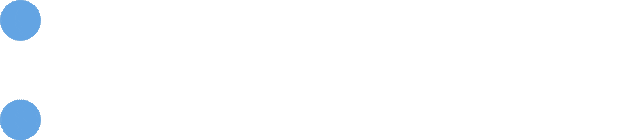
供稿:部新阶层处
编辑:吴薏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