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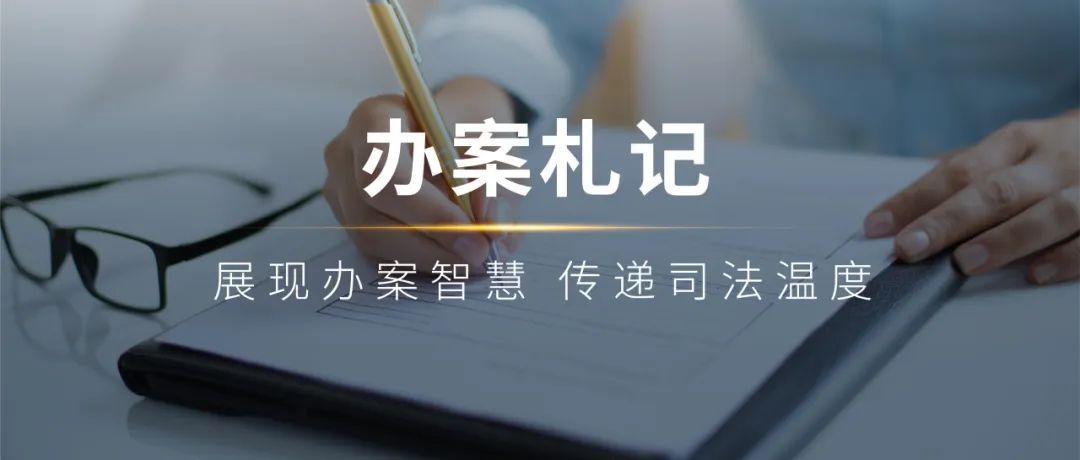
点击上方图片回顾专栏往期内容
那日,我翻开案卷时,手指不自觉地顿了顿——诉请金额一栏,一个数字后密密麻麻的“零”,像一串无声的惊雷。50000000元物业费、10000000元公益性收入……我开玩笑地说,这官司要是打到底,怕是连算盘珠子都得打冒烟。
二十年“糊涂账”,法庭里的火药味
故事得从1998年说起。
某小区建成时,被告作为小区前期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了二十多年的物业管理服务。近期,小区业委会针对选聘物业公司事宜召开业主大会,经征询全体业主意见后,业主大会决定更换物业公司。
谁料在准备交接时,一查旧账,双方直接炸了锅:业委会翻出前期物业合同,说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是“酬金制”,结余一分不能少;物业公司则拿出了和部分业主重新签订的协议书,提出双方已合意将“酬金制”进行了变更,咬定这些年是“包干制”,挣多挣少自己扛。

两边的算盘一打,按照两种不同的算法,不算其他费用,光物业费就差出50000000元!
第一次庭前会议,法庭里火药味呛人。
“二十年的账,你们现在才翻?早干嘛去了!” 物业公司说道。
“白纸黑字的合同,还想抵赖?” 业委会代表也不示弱。
我听着两边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心里直叹气:这哪是算账,分明是算旧仇。
审计耗时耗力,官司又叠官司
“二十年的票据堆成山,想要理清头绪恐怕得住在档案室里了!” 审计师一开口就叫苦。因双方调解差距实在过大,案子不得不进入审计程序。
听着审计师的诉苦,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蜗牛爬似的审计进度条,后背直发凉——一来审计耗时耗力,二来诉讼费、审计费滚雪球,再拖下去,业委会的公共收益怕是全要先去填这无底洞了。
更糟心的是,物业公司反手又告了一状,认为业委会为提起诉讼而召开的业主大会存在程序问题,从而另案提起业主撤销权之诉,要求撤销相关决定。一时间,一案变两案,法庭内外剑拔弩张。
我看着起诉状,苦笑:这哪儿是打官司,简直是打擂台。
破局的关键,是“划不来”
那天,审计师抹着汗找我:“法官,按这工作量,恐怕整个事务所不用干其他活了,审计费用也得奔着一百万去了!”
我攥着计算器,把双方成本一一罗列出来:先不说诉讼费和审计费,光说时间成本,法院开庭裁判得等审计结果下来,在这期间,物业公司的钱被法院冻着用不了,业委会看着这钱不仅拿不到手,而且还要先行垫付诉讼费用。双方能否结合现有的审计资料讨论讨论,看看是否有调解空间?
沉默许久,业委会代表突然嘀咕一句:“打官司……是挺划不来,我觉得么,双方还是有谈的空间的。”
就这一句话,让我嗅到了转机。
重开调解那天,我特意换了张圆桌。没了长桌的楚河汉界,两边的语气也软了三分。“咱都退一步,业主们不容易。”“我们根据账目票据测算下,尽量缩小下差距”。
拉锯战打了整整八轮。物业公司从“少一分免谈”到“再让两百万”;业委会从“必须全额”到“就当给业主们省点诉讼费”——六千万元的鸿沟,被一寸寸填成了羊肠小道。
法院的保险箱,装的是信任
金额最终定格时,新的难题又冒了头。业委会嘀咕:“这么大笔钱,他们赖账怎么办?”物业公司也嘀咕:“钱给了,他们翻脸不认咋整?”

“走法院代管款!你们信不过彼此,总信得过法院吧?”我说道。于是,物业公司的钱进了法院账户,业委会的收据盖了公章,我盯着银行流水上的数字,一个零一个零地数,数到第三遍才敢喘气——数千万元的和解费用,终究是稳稳落了地。
转账成功那晚,我站在法院台阶上,抬头看了看天。
二十年的“糊涂账”,针尖对麦芒,最后化解在一张圆桌、一把计算器,和一句“划不来”里。法条是冷的,可办案的人得暖着心——算得清钱,更要算清人心里的那杆秤。
主审法官

臧佳俊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来源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文字:臧佳俊、严国予
责任编辑:张巧雨
编辑:左雨欣
声明丨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高院”公众号
▴ 点击上方卡片关注“上海高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