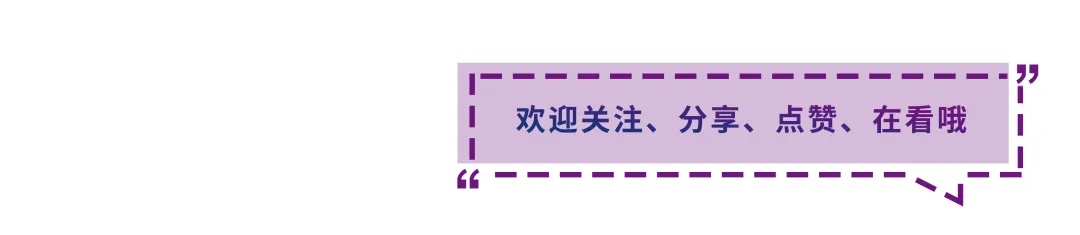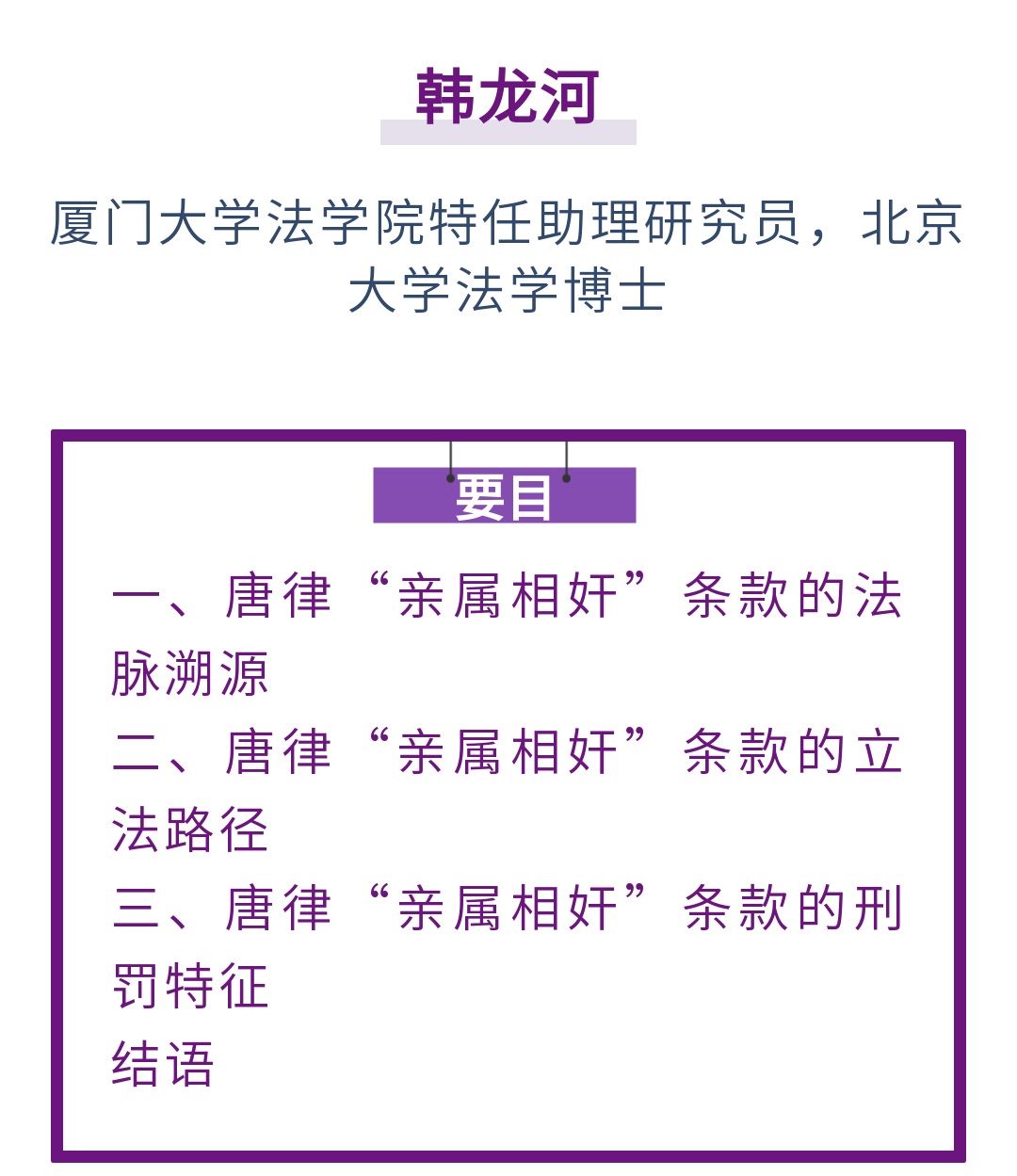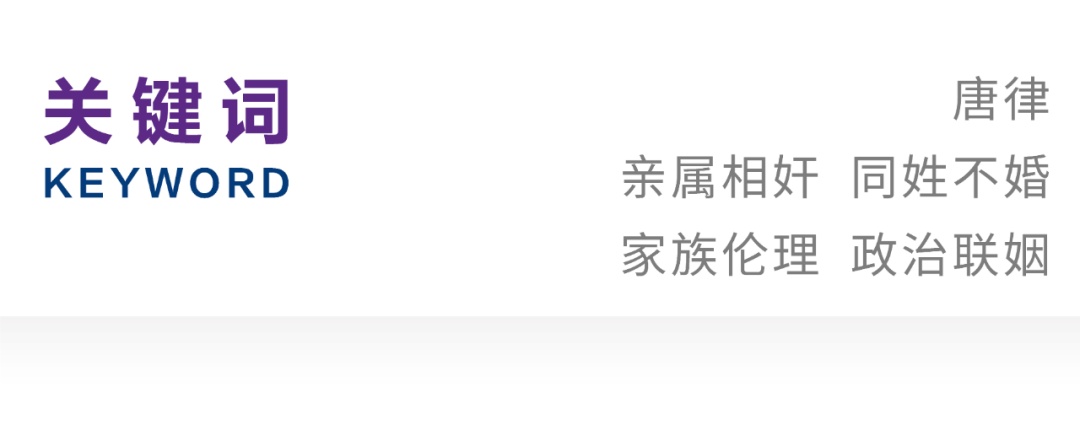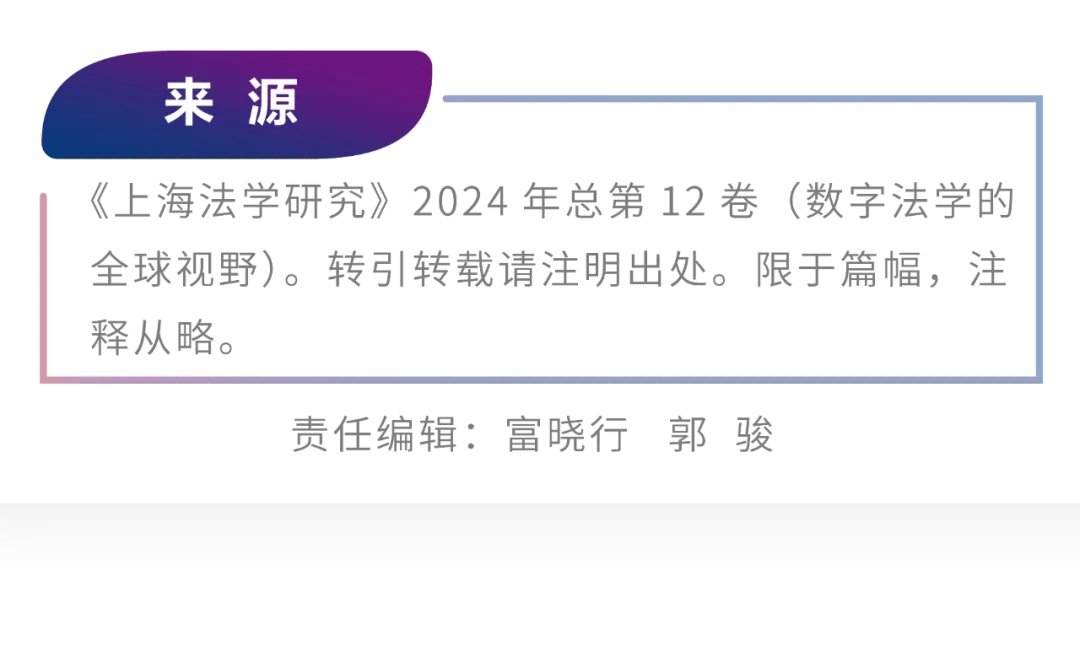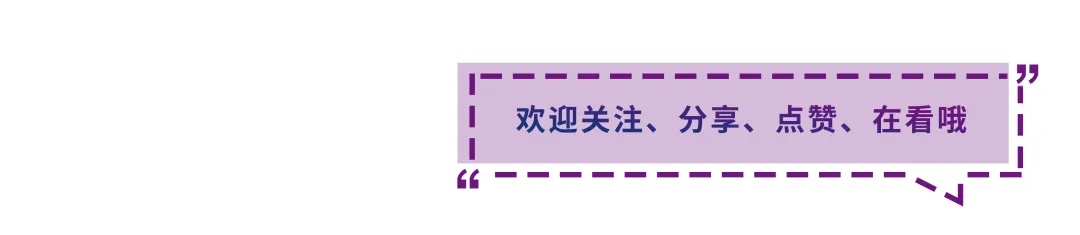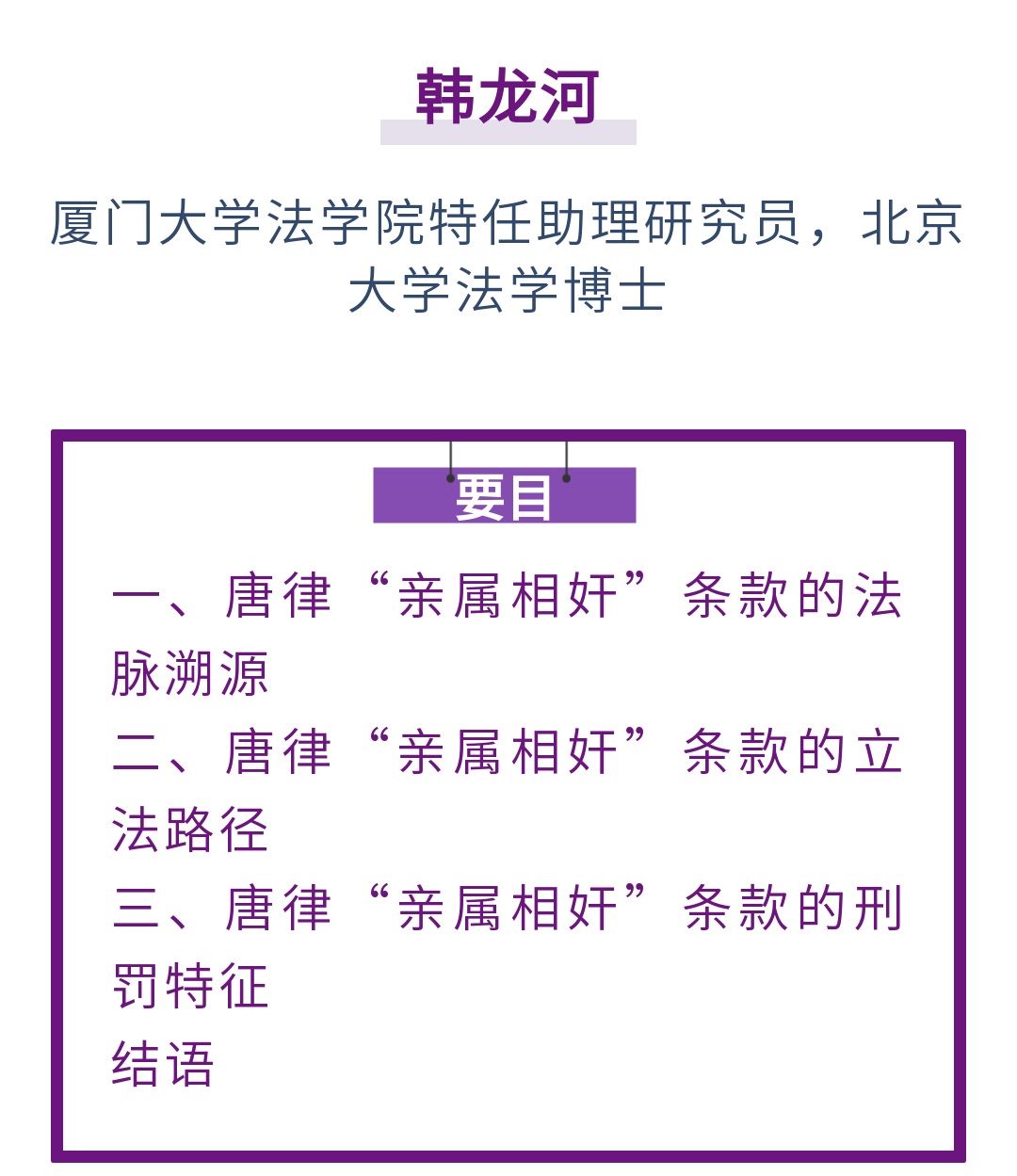

传统中国的“亲属相奸”法制规范以唐律作为承上启下的基点。基于法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唐律“内乱”词源及“亲属相奸”条款的深层架构显示了其对内维护家族伦理之导向,而非服叙制度,未对姑舅表亲婚进行规制则显示其对外促进政治联姻之目的。唐律对于“男女自由婚姻”“女性再婚”“民族通婚”等均较为宽容,而对于“亲属相奸”较为严苛,此与继承前朝律法及维护国家统治相关。在刑罚问题上,已入罪的“亲属相奸”行为的刑罚范围及轻重主要还是以家族伦理为主导,因而“亲属相奸”条款的总体刑罚既表现出严厉性的一面,也彰显出伦理性的一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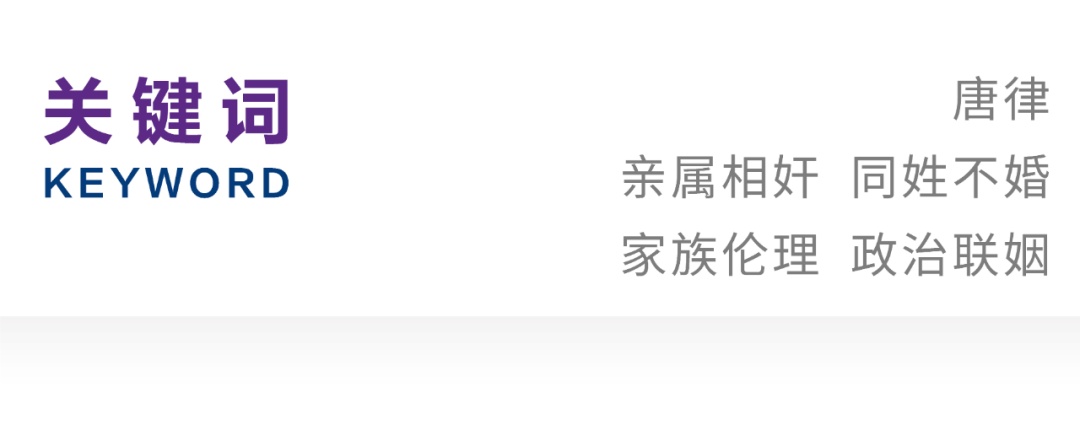
所谓“亲属相奸”,一般指代亲属间的性交或婚姻行为。古今中外对于“亲属相奸”行为普遍持反对态度,或强烈(在刑法层面加以规制),或温和(在道德或婚姻法层面加以规制),但对此现象背后原因的解释一直未有定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亲属相奸”与“乱伦”并不等同,“乱伦”主要泛指违反传统“五伦”之行为。自秦以迄清末,传统中国对于“亲属相奸”行为一直处较重的刑罚,只是历朝对于“亲属”的内涵和“相奸”的具体方式认定不同,因此展现出的法律规范也存在差异。综合观之,传统中国关于“亲属相奸”的法律规范是以唐代为转折点,唐之前的“亲属相奸”法律规范处于不断进化之中,至唐律而臻于完善,基本形成“亲属相奸”法律规范的定型蓝本,为后世朝代和诸多东亚国家所仿效。当前学界对于唐律“亲属相奸”条款的研究散见于“十恶制度”“奸罪制度”“亲属相犯”“婚姻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而作为重要伦常条款之一的“亲属相奸”条款所涉面较广,包括情欲、文化、规范等因素纠杂其间,现有的研究忽视了其独特的立法脉络。传统中国的文化与学术均是一脉相承常随着政权更迭而出现颠覆。在探究唐律“亲属相奸”条款的立法逻辑时务须溯源于此前的法律图景和法文化脉络。最早在法律层面对“亲属相奸”行为进行惩治的是秦律。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载了一条关于“亲属相奸”的问答,即“同母异父相与奸,可(何)论?弃市”。可知秦律对于同母异父的“亲属相奸”行为处以较严重的刑罚。汉承秦律,1980年出土的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杂律》记载了关于“亲属相奸”的一个条文,即“同产相与奸,若取(娶)以为妻,及所取(娶)皆弃市。其强与奸,除所强”。由于秦汉属父系氏族社会,故此处“同产”指代同父之兄弟姐妹,对于同父兄弟姐妹之间的性交与婚姻行为,均处死刑,存在强奸行为的,只处罚强奸者。《二年律令·复律》记载了关于“亲属相奸”的另一个条文,即“复兄弟、孝(季)父柏(伯)父之妻、御婢,皆黥为城旦舂。复男弟兄子、孝(季)柏(伯)父之子妻、御婢,皆完为城旦”。根据此条文,如果与叔伯兄弟的妻子或御婢结婚,则男女将被刺面并判处徒刑;如果与叔伯兄弟之子的妻子或御婢结婚,则男女都将被判处徒刑。事实上,此条文是对先秦时期“柔报婚”的一种否定和归罪。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代有所谓“禽兽行”的罪名,主要针对“亲属相奸”“尊卑相奸”和“人兽相奸”行为,对于“禽兽行”,一般处以较严重的刑罚。事实上,汉代王室存在诸多“亲属相奸”事例。例如,根据《史记·荆燕世家》记载,燕王刘定国与父亲的姬妾、自己的子女通奸,被举报犯了“禽兽行”,后畏罪自杀,封国被除。根据《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记载,安城思侯刘寿光在汉宣帝五凤二年,因与姐姐通奸而获罪,后在狱中病死;根据《廿二史諸记》记载,衡山王孝与父侍婢奸,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梁王立与姑园子奸。秦汉之后,两晋时期第一次将礼制中的“五服制度”纳入刑律之中,作为量刑时判断亲疏尊卑的主要标准。而对于“亲属相奸”问题,晋代明确“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时期,《北周律》首次将“亲属相奸”行为置为“内乱”之罪,而《北齐律》首次将“内乱”罪置于“重罪十条”之中。《隋律》承继《北齐律》,将“重罪十条”转为“十恶”,对“亲属相奸”行为予以严惩。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室贵族内部出现诸多“亲属相奸”事件。例如,《魏书》记载了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淫乱无度,与其母路氏通奸;南朝宋皇帝刘子业与亲姐及姑母通奸等事件。而《北齐律》之所以将“内乱”置于“重罪十条”,主要原因是当时胡族当政,对于家族伦理不加重视,导致“亲属相奸”事件频发,而《北齐律》制定者主要为儒家学者,他们感慨于现世礼法之颓,尤其是“禽兽其行”愈演愈烈,故而严厉规范之。探究唐代“亲属相奸”条款的法制源流,更为重要的是探究制度背后的法文化脉络。此种法文化脉络既是一脉相承又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前行。虽然在传统中国的法制框架中,“亲属相奸”和“同姓不婚”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但二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二者都是对亲族或亲属相结合的行为进行规制。对于“同姓不婚”而言,主流学说认为“同姓不婚”的形成原因是出于“优生学”的考虑,但这种论断难以解释的是为何传统中国一直未对姑舅表亲婚加以规制。而且,在《唐律疏议》中,“同姓不婚”条的疏议认为“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可见“同姓不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违背伦理秩序。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侯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在王国维看来,周朝由边远部落发展而来,其维护统治的主要方法是对内采用宗法伦理规范之,对外则以异姓结合的方式联合之,因而在此政策背景下形成的“同姓不婚”体现为对内维护宗族伦理和对外促进政治联姻的功用,而最终目的为维护国家统治。事实上,自周代以降,传统中国一直延续“家国同构”的统治方式,“家”和“国”在结构和功能上趋于同质化。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中,“亲属相奸”与“同姓为婚”异曲同工,既可能损害家族抑或国家的等级秩序,也可能损害家族抑或国家的政治联姻问题。只不过,与“同姓为婚”相比,“亲属相奸”对于家族伦理以及政治联姻问题的危害更大。具体言之,秦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法制多受儒法两家影响,在维护家族等级秩序上,儒家主张贵贱、亲疏、长幼、尊卑有别,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法家虽认为一切的人在法律面前均须平等,但并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及存在。是故,受儒法两家影响的传统法制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维护家族等级秩序,而维护家族等级秩序的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国家统治。由于“亲属相奸”行为严重损害家族等级秩序,因而为传统法制所严惩。除了对内维护家族伦理外,禁止亲属结合可以扩大与外族结合的概率,以巩固家族和统治阶级的实力,最终为维护国家统治服务,从秦汉之后的律法没有对姑舅表亲婚进行规制可见一斑。如果仅仅是为了维护家族伦理,则“亲属相奸”条款应该囊括姑舅表亲婚,而之所以未对姑舅表亲婚进行惩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姑舅表亲婚对于促进政治联姻的重要性。对于皇室而言,无论是娶母族还是姑族,均有利于维护皇族血统的纯正和身份的高贵,且有利于结合外族势力,以强大统治阶级的力量。对于民众而言,姑舅表亲婚不仅是一种婚配资源的交换,而且是一种亲上加亲的做法,有利于巩固家族的团结和兴盛。对于“亲属相奸”问题,唐律在前世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规范,在篇章结构和生成逻辑上均具典型性。唐律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唐朝的所有律。其中,《唐律疏议》保存最为完好,也最具代表性。以往观点多认为《唐律疏议》中“亲属相奸”条款主要包括《名例律》中的“内乱”和《杂律》中的“奸缌麻以上亲及妻”条、“奸从祖母姑等”条和“奸父祖妾等”条。事实上,还应包括《户婚律》中的“同姓为婚”条和“尝为袒免妻而嫁娶”条。对于《名例律》中“十恶”之“内乱”,其具体律文为“十曰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依据疏议,“奸小功以上亲”,指男性与小功及小功以上女亲属相奸,如果女性相对男性只有缌麻之亲,虽然男性相对女性有小功之亲也不在此列,如外孙女之于外祖父和外甥女相对于舅舅。“父祖妾”包括父祖之妾及媵,有无孩子都一样。“及与和者”,与男性和奸的女性也归入“内乱”之罪,包括被强奸后与男性和奸者,如果只是被强奸,则只处罚男性。对于《杂律》之“奸缌麻以上亲及妻”条,其具体律文为:“诸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及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强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妾,减一等。(余条奸妾,准此。)”依据疏议,如果男性与缌麻以上亲属或亲属之妻和奸,和妻子前夫女儿、同母异父姐妹和奸,则二人均需被罚三年徒刑。如果是强奸行为,则将强奸者流放二千里。如因强奸致人损伤,则将强奸者判处死刑。如果前文之“妻”转为“妾或媵”,则比照“妻”罪减一等。其他五服之内的奸罪,如果只有奸名而无妾罪,则比照此条减妻一等。如果是主家之奴隶与妾奸,也依此条减妻一等。对于《杂律》之“奸从祖母姑等”条,其具体律文为“诸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母姑、从父姊妹、从母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强者,绞”。依据疏议,“从祖祖母姑”,为祖父的兄弟的妻子,和祖父的姐妹;“从祖伯叔母姑”,指父亲堂兄弟的妻子和父亲的堂姐妹;“从父姐妹”,指自己的堂姐妹;“从母”,指母亲的姐妹;“流二千里”和“强者,绞”,如果是和奸行为,则将二者流放二千里;如果是强奸行为,则将强奸者判处死刑。对于《杂律》之“奸父祖妾等”条,其具体律文为“诸奸父祖妾、(谓曾经有父祖子者。)伯叔母、姑、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女者,绞。即奸父祖所幸婢,减二等”。依据疏议,“父祖妾”指代父亲和祖父(包括曾祖和高祖)的妾;“谓曾经有父祖子者”,指有为父亲和祖父生育孩子的妾,如果没有生育过孩子,则比照前文的“妾,减一等”定罪量刑;“即奸父祖所幸婢,减二等”,如果和父亲或祖父所临幸过的婢女和奸,无论是否有孩子,均减二等论罪,即三年徒刑。此条律文未提强奸行为,依照类推原则,强奸行为会比照和奸行为罪加一等。此外,对于《户婚律》中的“同姓为婚”条和“尝为袒免妻而嫁娶”条,一方面是因为二者主要规范与同姓且同宗之亲属、无服之亲属、无服亲属之妻、缌麻亲属之妻等重要服制亲属外之亲属结婚的行为,虽无涉及奸罪,但仍关乎亲属间之嫁娶;另一方面是因为二者均规定了亲属间违律为婚涉及重要服制亲属时“以奸论”,补充了《杂律》三条“亲属相奸”条款对于违律为婚行为的欠缺规范(只规范和奸和强奸行为);因而隶属于“亲属相奸”条款行列。唐律共十二篇,十二篇之间逻辑关系紧密,且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调整功能。依据上文,唐律“亲属相奸”条款主要分布于《名例律》《户婚律》《杂律》中。在层次结构上,《名例律》作为总论篇被置于首位,“十恶”之“内乱”主要对“亲属相奸罪”进行总揽;《户婚律》和《杂律》主要承载规范婚姻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职能,主要对“亲属相奸罪”进行具化,包括不同等级亲属间的违律为婚、强奸、和奸等行为。从罪行的严重程度上,《户婚律》之“同姓为婚”条和“尝为袒免妻而嫁娶”条在规范重要服制亲属外之亲属时,论罪较轻,涉及重要服制亲属而“以奸论”时,比附《杂律》三条“亲属相奸”条款论罪;《杂律》之“奸缌麻以上亲及妻”条、“奸从祖母姑等”条和“奸父祖妾等”条依亲属等级递增而论罪愈重,其中“奸从祖母姑等”条和“奸父祖妾等”条主要在“奸缌麻以上亲及妻”条的基础上划出更为重要的亲属而加重刑罚;“内乱”主要将《杂律》三条“亲属相奸”条款中的“小功以上亲属和父祖妾”划分出来并冠以“内乱”之名,以作为“十恶”之一的重罪。基于传统中国法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唐律对于“亲属相奸”行为的规范并非出于优生目的,而是在“家国同构”的统治框架中,以维护国家统治为纲,以对内维护家族伦理和对外促进政治联姻为目。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唐律疏议》对于“亲属相奸”行为的严格性与唐前期“性观念”的开放性相背而驰。具体言之,唐前期由于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习气的遗存(唐皇族本身也为胡族血统),加之唐经济和文化的开放,当时社会对于男女间的性行为和婚姻行为形成了一种较为包容的风气,不仅可以随意讨论,而且男女自由结婚、女性再嫁、隔辈婚姻、民族间通婚等均普遍存在,唐律对此也不加规制。在此种包容的社会风气下,为何于《唐律疏议》中对“亲属相奸”行为进行严格规制?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唐律对于《北齐律》和《开皇律》的承继。《北齐律》代表南北朝立法的最高水平,为规范“禽兽行”的愈演愈烈而将“内乱”置于“重罪十条”中,而《开皇律》将其化为“十恶”之目,唐律继承隋律,因而对于“亲属相奸”行为予以严惩。其二是维护统治之需。《唐律疏议·名例律》中言“礼者君之柄”,但实际上唐律对于礼制的维护和引用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的,而此种选择性的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统治。唐建国初期,前朝大规模工程的损耗和多年战乱导致人口凋敝,而人口稀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赋税的征取。唐律对于男女自由恋爱形成的婚姻的维护、对于女性再婚的宽容、对于民族通婚的接纳均有助于人口数量的恢复,民族通婚还有助于在当时复杂的多民族环境下促进民族和睦,因此伦理之严让位于国策之需。而“亲属相奸”行为严重破坏伦理纲常,破坏家族等级秩序,且不利于政治联姻功能的施行,弊大于利,因而未为政策所采用,而为唐律所严惩。对于促进政治联姻而言,唐律“亲属相奸”条款对于姑舅表亲婚不加规制已然说明其促进政治联姻之意图。《唐律疏议》的“同姓为婚”条之疏议曰:“其外姻虽有服,非尊卑者为婚,不禁。”事实上,传统中国一直有“门当户对”的嫁娶观念,唐代也不例外。唐律中的“奴娶良人为妻”条、“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等均禁止跨越阶级的婚嫁。易言之,子女婚嫁属于家族的政治资源,需要“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由尊长统筹,一般选择在同阶层之间嫁娶,以便形成政治联姻。由于姑表亲、舅表亲和姨表亲一般处于同一阶层,且出于亲上加亲的传统理念,唐代无论是上层阶级还是普通百姓,均普遍存在通过姑舅表亲婚缔结政治联姻之例子。对于维护家族伦理而言,则可以从“内乱”词源和“亲属相奸”条款的深层架构彰显。“十恶”之十为“内乱”,疏议曰:“《左传》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若有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疏议借用《左传》之语阐明“内乱”之意涵,即家族内男女应各安其分,不得扰乱家族内部规则,若有亲属相奸、紊乱礼教之行,则应受刑严惩。《北周律》虽然不置“十恶”之目,但最早将“内乱”作为罪名对“亲属相奸”行为进行严惩。《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准五服以制罪”的典范。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唐律疏议》对于一般“亲属相犯”类的案件会区分尊长卑幼而量刑有别,而对“亲属相奸”和“亲属相盗”两类案件只论服叙,不论尊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主要从“亲属相奸”条款的字面含义推之,如果从条文的深层架构观之,则显示出《唐律疏议》“亲属相奸”条款是以家族伦理为导向,包括尊卑,而非服叙制度。前文述及,《唐律疏议》对于“内乱”的规范是以“紊乱礼经”为纲,以“禽兽其行,朋淫于家”为具体罪行。在《杂律》的三个“亲属相奸”条款中,所涉及的亲属范围也并非以服叙制度为导向。例如,“奸缌麻以上亲及妻”条中“诸奸缌麻以上亲之妻”可能为无服;处刑最重的“奸父祖妾等”条中“父祖妾(谓曾经有父祖子者)”和“孙之妇”仅为缌麻亲,而本条其他亲属均为期亲(唐代期亲等同于齐衰)或大功亲。由此观之,有些亲属服叙虽轻,但伦理却重,因而为“亲属相奸”条款所具体规范。在尊卑问题上,虽然“亲属相奸”条款本身未明示依据长幼尊卑进行惩处,但“亲属相奸”与“亲属相告”在司法实践中是并用的,特别是卑幼告发尊长比尊长告发卑幼的处刑要更重。具体言之,“亲属相奸”条款对于和奸男女的刑罚是一致的,对于强奸则只坐强奸者。在家族中,尊长强奸卑幼具有权威上、时间上和空间上之便利,而卑幼受到侵犯后若告发尊长则要付诸重大的法律代价,也会遭到社会伦理的指摘,故而尊卑秩序对于“亲属相奸”案件的发现和惩处是具有一定影响的。前文述及,“亲属相奸”条款还应该包括《户律》中的两条律文。此两条律文说明唐律规范“亲属相奸”行为的全面性和维护家族礼制的严厉性。其中,“同姓为婚”条的疏议阐明了“亲属相奸”行为对于家族伦理的严重损害,如“同姓之人,即当同祖,为妻为妾,乱法不殊”“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而之所以将“同姓不婚”限制于同宗,一方面原因在于疏议所言“祖宗迁易,年代浸远,流源析本,罕能推详”,另一方面在于限制所有同姓间不得为婚将影响当时人口增长,也不利于宗族之间的交流往来。总体而言,唐律“亲属相奸”条款的立法路径不以优生目的为宗,而是在“家国同构”的统治框架中,以维护统治为归宿,以对内维护家族伦理和对外促进政治联姻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刑罚问题上,由于政治联姻主要影响的是“亲属相奸”条款的入罪范围,对于已入罪的“亲属相奸”行为,其刑罚范围及轻重主要还是受家族伦理主导,因而“亲属相奸”条款的总体刑罚既表现出严厉性的一面,也彰显出伦理性的一面。下文将“亲属相奸”条款置于“十恶”、奸罪、“亲属相犯”的罪名体系下,以观测其严厉性和伦理性两个特征。《唐律疏议》将较为严重的“亲属相奸”行为归入“十恶”。所谓“十恶”,疏议曰:“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戒。”“十恶”意指唐律中最重要的十类犯罪行为,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每种均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损害,被特别标注于篇首。据考证,“十恶”之名来源于佛教。佛经中也有“十恶”之名,包括“杀”“盗”“淫”“妄言”“绮语”“恶口”“两舌”“嫉妒”“恚害”“邪见”,虽然与唐律中的“十恶”不相一致,但并指十类重要的罪行。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极大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伴随着佛教的兴盛,“十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喻指重大恶行,并在立法时被用作法律用语。“十恶”虽指代十种重罪,但每项所内含的具体罪名存在差异。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既是“十恶”之“恶名”,也是具体罪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虽是“十恶”之“恶名”,但每项均包含数类具体罪名;比较特殊的是“内乱”,既是“十恶”之“恶名”,也包含数个具体罪名,但仅有一类,即奸罪。“十恶”之罪,皆为违背传统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行为,是法律礼教化的一种体现。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不睦”等虽违背传统纲常礼教,但更多属于“自然犯”,即使未违背礼制也应该被归入严重犯罪。相反,“大不敬”“不孝”“内乱”等则更多属于“法定犯”,主要因为违背礼制而被归入严重犯罪。“十恶”之中,“内乱”虽被置于最末,但唐律对其科刑并非最轻,甚至可以说其在“十恶”各项内容所包含的具体犯罪行为中,科刑是比较重的,因为“内乱”之中对死刑的适用是比较普遍的,如奸期亲、奸父祖妾等皆科以绞刑。唐律中,依照犯罪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奸罪可区分为无身份关系之奸罪和有身份关系之奸罪。对于无身份关系之奸罪而言,主要包括“良人相奸”和“僧道相奸”,二者的具体犯罪人之间均不存在隶属或尊卑关系。对于有身份关系之奸罪而言,主要包括“良贱相奸”“亲属相奸”“家贱奸主”和“监临官奸部民”,四者的具体犯罪人之间存在一定的尊卑、隶属和监管关系。唐律奸罪体系中,每种奸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存在差异。其中,“良人相奸”和“僧道相奸”主要对规范化和体制化的社会机制造成损害,因而破坏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良贱相奸”“家贱奸主”“亲属相奸”主要对既已形成的等级和尊卑关系造成损害,因而破坏的是社会和家族等级秩序;“监临官奸部民”主要指代监临官利用职权在监守内与部民奸,因而破坏的是国家行政纪律。在一般刑罚上,唐律奸罪体系是以“良人相奸”的刑罚为基础,依据犯罪人的身份和犯罪手段逐次递增刑罚。其中,“良人相奸”“僧道相奸”“良贱相奸”和“监临官奸部民”的刑罚相对较轻,以徒刑为主;“亲属相奸”“家贱奸主”的刑罚较重,以流刑和绞刑为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亲属相奸”“家贱奸主”对于家族伦理和社会等级秩序的严重破坏,性质较为恶劣。在特别刑罚上,奸罪体系中的“内乱”被排除在议、请、减之外,“监临官奸部民”被排除在请、减之外。对官员而言,犯“内乱”和“监临官奸部民”之罪则官爵悉除。之所以施以特别刑罚,一方面因为“内乱”属于“十恶”之一,性质较为恶劣;另一方面因为议、请、减主要针对有一定身份的官员及其亲属,奸罪体系中之“监临官奸部民”属于官员利用职权之便的犯罪,对于国家行政纪律和监守内部民权利损害较大。值得一提的是,“亲属相奸”在刑罚上主要以伦理之轻重为量刑依据,因而对于“有夫奸”和“无夫奸”的处罚是一样的,而“良人相奸”的刑罚主要以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损害为量刑依据,因而对于“有夫奸”的处罚要比“无夫奸”重。同理,“亲属相奸”条款对于和奸男女的处罚是一致的,而“良贱相奸”条款对于良人的处罚要比贱人的处罚轻,主要因为“亲属相奸”的刑罚裁量以伦理之轻重为主导,而“良贱相奸”的刑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维护优势阶级)。此外,唐律奸罪体系内的所有奸罪均不适用共同犯罪的首从判断标准,因为“和奸”属于双方“同时犯”,不分首从,而“强奸”只处罚强奸者,更不分首从。同时,对于唐律奸罪体系内的所有奸罪的自首均不予减免刑罚。此外,妇女若犯奸罪,丈夫可以不顾唐律之“三不去”而解除婚姻。若有人“夜无故入人家”犯奸,即使主人已明知,仍然允许其对犯奸之人予以杀伤。若在外遇到强奸行为,允许旁人进行抓捕,遇到抵抗还允许旁人对强奸者进行杀伤。若遇到外人与同籍内之人和奸,允许同籍内之他人进行抓捕,遇到抵抗还允许进行杀伤。但是,若遇到亲属间的和奸行为,如遇到者与其亲属关系在“亲亲相隐”的范围内,则不允许对犯奸者进行抓捕。唐律“亲属相犯”体系中,依照侵犯的对象进行区分,主要包括三类犯罪行为:第一类为亲属间人身侵犯犯罪,包括“亲属相杀”“亲属相殴”“亲属相奸”等;第二类为亲属间财产侵犯犯罪,包括“亲属相盗”等;第三类为亲属间身份侵犯犯罪,包括“告言诅詈”“供养有阙”“居丧嫁娶作乐”等。唐律中有普通杀、殴、奸、盗等的罪刑律文,主要以违背社会管理秩序为处刑标准。对于“亲属相犯”而言,主要以违背家族伦理为处刑目的,属于普通犯罪之外的特殊犯罪,类似于“法定犯”,因而定罪和量刑均存在特殊性。三类“亲属相犯”犯罪中,人身侵犯犯罪的处刑最重,以绞刑和斩刑为主,且“恶逆”“不睦”“内乱”均位列“十恶”;身份侵犯犯罪次之,以徒刑和绞刑为主,且“不孝”位列“十恶”;财产侵犯处罚最轻,以笞刑、杖刑和徒刑为主,主要因“亲属相盗”比照“凡人相盗”处罚更轻。因为唐律对于“亲属相犯”犯罪的处罚是以维护家族伦理为导向的,亲属间的杀伤与奸对于家族亲属安危和等级秩序等具有直接的损害,因而处罚最重;告诅尊亲属、未尽赡养义务、在丧期嫁娶等对于家族亲属的生活保障、名誉等造成损害,因而处刑次之;亲属间之强盗或窃盗行为对于家族总体财产未形成具体损害,因而处刑最轻。唐律“亲属相犯”相较于“凡人相犯”体现出同罪异罚的特征。其中,“亲属相杀”和“亲属相殴”中卑幼杀害、殴打尊长的处罚比凡人之间相同犯罪的处罚重,反之则轻;“亲属相盗”的总体刑罚较“凡人相盗”轻;“亲属相奸”的总体刑罚较“凡人相奸”重。因为唐律“亲属相犯”处刑是以家族伦理为导向的,卑幼杀害或殴打尊长损害了家族的等级秩序和尊长的权威,为伦理所不容,因而处刑比凡人重,而尊长杀害或殴打卑幼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尊长的威慑力,因而处刑比照凡人轻;“亲属相盗”并不违背“亲属共财”之伦理,因而总体处刑比照普通贼盗轻;“亲属相奸”严重损害家族的伦理关系,因而总体处刑比照凡人重。唐律对于“亲属相犯”犯罪是区分尊长卑幼而量刑有别。其中,若卑幼杀害、殴打、告发尊长,则服制愈近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处罚愈轻,若尊长杀害、殴打、告发卑幼,则相反;“亲属相盗”体现为尊长的处罚比卑幼轻;“亲属相奸”体现为和奸时尊长和卑幼的刑罚一致,强奸时卑幼受到的刑罚压力更大。因为唐律“亲属相犯”的处刑以家族伦理为导向,为维护尊长在家族中的威慑力和权威性,尊长犯卑幼与卑幼犯尊长的处刑自然不同,且与亲属等级关系相勾连;“亲属相盗”中尊长具有管理财产之权威,因而尊长比照卑幼处刑轻;“亲属相奸”中尊长与卑幼和奸时并不能彰显尊长的权威,因而尊长和卑幼处刑一致,但尊长具有强奸卑幼的便利,且迫于“亲属相告”之并用,因而卑幼所面临的刑罚压力更大。唐律“亲属相奸”条款除了《名例律》之“内乱”和《杂律》的三个条文外,应当包含《户婚律》的“同姓不婚”条和“尝为袒免妻而嫁娶”条。唐律“亲属相奸”条款在层次结构和罪行严重程度上构成内在逻辑明晰和严谨的框架。在律文生成逻辑上,唐前期的“性观念”较为开放,而对于“亲属相奸”问题仍给予严厉的惩罚。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唐律对于《北齐律》和《开皇律》的承继;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国家统治(促进人口增长)之需。唐律“内乱”词源和“亲属相奸”条款的深层架构展示其对内维护家族伦理的目的(非服叙制度),而未对姑舅表亲婚进行规范则体现了其对外促进政治联姻之功能。唐律“亲属相奸”条款的刑罚之于“十恶”、奸罪、“亲属相犯”而言,既存在共性,也存在独特性。由于政治联姻主要影响的是“亲属相奸”条款的入罪范围,对于已入罪的“亲属相奸”行为,其刑罚范围及轻重主要还是受家族伦理主导,因而“亲属相奸”条款的总体刑罚既表现出严厉性的一面,如“内乱”的死刑适用较为普遍、相比于其他奸罪或“亲属相犯”犯罪处刑更重等;也彰显出伦理性的一面,如不区分有夫奸和无夫奸、不允许亲属参与抓捕、和奸时尊长和卑幼的刑罚一致等。唐律作为传统中国法典的楷模,对后世朝代和东亚国家(包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的律法均产生重要的影响,是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唐律对于“亲属相奸”行为的规范也为后世朝代和东亚国家所承继,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因时、因地制宜,根据统治所需和自身法制环境形成了相应的“亲属相奸”法制规范,使得唐律“亲属相奸”条款的立法逻辑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续。陈姝 叶佳|执行异议之诉中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实证研究——兼论新《公司法》施行后出资加速规则的衔接适用
王耀海|马克思主义法学及其适域
赵园园|算法赋能社会信用治理的反思与重构
马钱丽|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海员工会参与船员队伍治理的启示
赵智兴|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李慧敏|数字经济背景下网络平台的自我规制:基本构造、模式变迁与路径完善

上海市法学会官网
http://www.sls.org.cn